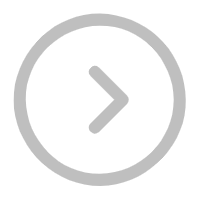导语“我对自己位置的反思在于,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她们跟我聊对职业的迷惘,后来我不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
 文章来源:全现在 作者:党元悦
文章来源:全现在 作者:党元悦
社交媒体研究者董晨宇“迷”上了看直播。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这成为了他工作的一部分。
董晨宇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作为一名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一直以来,他的研究都聚焦于社交媒体和背后的用户。2020年,他和合作者把关注点放在了秀场主播上,希望了解主播、观众以及直播平台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线上做了半年多的田野调查,董晨宇自己化身直播间的“场控”,帮助主播们维护直播间秩序,深度接触了许多主播、观众以及主播公会的运营人员,最终勾勒出了主播行业的大致图景。
前些日子,董晨宇买了一位主播做的手工品。这位主播曾经告诉董晨宇,运营跟她说“所有人都是假的,互联网就是假的”,但她觉得不是。对她来说,每个观众都是她的朋友,是真实存在的人。她一直播下去,是想知道,“我就是这样想的又怎样?我凭什么就比你们播得差?”而结局是,这位主播没能撑下去,最后退出了直播行业,开始兼职卖手工品。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都藏在董晨宇厚厚的田野笔记里,或许不会被更多人知晓。但这些千姿百态的个体经历,一次次提醒董晨宇:在研究中,他所面对的不是屏幕里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同的生活境遇,最终把她们拉到了手机摄像头前,从事这样一个承受着诸多社会偏见的职业。
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董晨宇把主播对观众的维护和讨好视为一种“关系劳动”。主播在直播中向观众“售卖”的,是一种亲密关系。观众对于主播所投入的情感,则“时而真实、时而虚幻,无时无刻不需要通过‘续费’来维系和发展”。而董晨宇自己,也因为和主播成为朋友,而与她们产生了情感上的勾连。这让他意识到,直播所制造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即使作为研究者也无法免俗。
2021年初,董晨宇与全现在聊起了他在研究中所见到的直播百态、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背后的运行机制,还有他对自己研究者身份的反思。
01 直播不是“一个骗子骗一群傻子”
全现在:你们的研究是去年三月开始做的,当初为什么会把注意力放在直播行业上?
董晨宇:其实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过程。当时我们在做线上社交媒体的用户研究。我们想知道,举个例子,同一件事发在豆瓣、微博、朋友圈这三个平台上,用户会略做修改,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疫情来了,这些平台的内容高度同质化,全部都是疫情,数据没办法收集了。我们就决定换一个线上能做的其他主题。我看到了直播,不需要跑线下,也不会受到疫情影响。甚至有一种说法是,疫情对于直播行业可能是间接的推动作用,因为线下的娱乐变少了。
全现在:你们在研究中观察到了主播们的哪些特点?
董晨宇:主播到底是个什么存在?是明星吗?是公共人物吗?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公众人物,因为一个直播间里,她可能有五千个粉丝,一万个粉丝。但问题在于,她跟吴彦祖不一样。吴彦祖演什么,你看什么。主播是观众聊什么,你跟着做什么。所以主播的这种表演我们称之为叫做co-performance,叫联合表演。这个表演是由观众跟主播一块完成的。
有一个主播,直播间里有两个男观众,特别爱聊股票,俩人来直播间就聊股票。主播一脸懵,想扭转话题,其中一位男观众直接刷了个礼物,说你先不要说话,你在这儿坐着就可以。
主播具有公众人物的一些特点,被许多人所关注,但其中认识的是少数。她的权力是倒转过来的,由观众所决定。在当今时代,这种倒转过来的权力流行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我看过一篇论文,有一句话特别精彩,大意是在最早期,明星在电影屏幕当中,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仰视;到了电视时代,我们是平视;手机时代,我们是俯视。这是权力变化的一种隐喻。
对于观众来讲,主播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总体来讲仍然是个性别化的议题。男性对于女性的凝视和消费,这个是逃不开的。我们在正在写作的英文论文当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暧昧经济。暧昧成为了一种收入来源。
对于一掷千金的“大哥”(即直播间内打赏较多的男性)而言,很多时候他们玩的就是一种暧昧。甚至有一个“大哥”跟我说,如果主播跟他表白,他第二天就退出直播间。我说为什么?他说结果并不重要,暧昧的这个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
但也不能用暧昧来总结所有的男观众。我自己觉得里面的关系有三类。第一类我称之为虚拟陪酒,直播间其实就是个虚拟夜总会。第二种是电子兄妹,对主播的感情不是我戏弄你、耍你或者跟你搞暧昧,而是我真的拿你当一个妹妹或者朋友。说兄妹的原因是大部分具有打赏能力的观众,年纪都会比主播大。很少见到25岁的小伙子给40岁的主播一掷千金。第三种是平民偶像,想陪着主播见证她一步步变得更好,是一种养成系的游戏。当然大众媒体报道的时候,基本上是简化为虚拟陪酒。但是这个行业的生态,比我们想的更加复杂,观众的动机非常多元。
全现在:观众对主播的打赏,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董晨宇:如果我们把情感上的诚实作为一个指标,其实打赏有负效果。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是我的场控,你给我打的赏很少,完全不能支撑我活下去,但是你每天陪着我直播,有什么事情提醒一下我,这时候我会对你更真诚。但如果你每天给我打赏2000块钱,打上一个月,我敢对你特别真实吗?我不敢,我想的是如何让你第二个月继续支持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套路你,因为没有人是傻子,于是我的策略就叫做“表演性真实”。我去表演,让你觉得我对你很真实。所以往往大额打赏可能对主播跟观众之间的情感诚实是有负效果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做参与式观察的时候,觉得这个主播特别难,甚至看到主播哭。我完全有能力给她打赏几百块钱,帮她一把,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会改变我们的关系。一旦我给她们打赏了很多,她们就不可能把我看作一个研究者,对我保持现在的真诚了。
但是不送礼物也是不行的。送礼物也是参与的一部分,我来到直播间,做研究、发论文,甚至获得名誉,对于主播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也算是一种微薄的回馈吧。
当然,打赏得多的话,你在直播间里会坐拥皇帝一般的感觉,但这是演出来的。我跟一个主播聊天,我说我突然觉得直播平台就是一个电视台,以前是电视台24小时内塞节目进去,就那么几个台,没多少地方,塞不了太多。现在你随便找个人就可以演节目,别人的节目是唱歌、跳舞、演小品,你的节目是尬聊。尬聊也是种才艺,所以你就是个演员,直播间的东西都是演出来的。
全现在:这样的“表演”如何变现?
董晨宇:这个行业卖什么?它没产品,卖的就是关系。我看你直播是因为唱歌好听吗?不是。我为什么不看陈奕迅直播?我看你直播是因为你有才艺吗?也不是。我看你直播是因为我觉得跟你有感情,我很寂寞,找个人聊天。这是一种陪伴感。而陪伴感对应的就是主播会管你叫家人。但是家人为什么会给你钱呢?这就靠一个机制,叫做PK。PK会把主播送到绝境当中。
两个主播说谁票少,往脖子上画十只乌龟。我们愿意家人脖子上画乌龟吗?我们肯定不愿意,所以我们去上票,让她赢。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家人的困境是虚设的,其实不存在。有个观众跟我说,这不是自找的吗?我让你做了吗?用这种卖惨的方式去唤起我们的关系,造成一种失调:我们关系很好,你现在深处困境,我如果见死不救,没有任何表达,心里会有内疚感。靠这种内疚感,可能会有更多的礼物。
全现在:你刚提到陪伴关系,现在不止是直播间里有,似乎在网络上,购买“虚拟男友”或者“虚拟女友”,还有连麦等等形式,在年轻人当中也开始流行。
董晨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孤独的时代。这种孤独体现在很多地方。首先是社会压力很大。第二,人们有了钱之后同时有巨大的虚无感。有一个观众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蛮高的,在某一线城市还有好几套房。他跟我说,去酒吧太累了,要穿衣服打扮自己,而他去直播间很简单,躺床上,打开手机就开始聊天,这是多么好的消遣的方式。他所要的就是陪伴感。很多观众看得很明白。
媒体有一点非常误导的地方——他们把观众塑造成傻子了。他们不傻的,甚至我觉得很多观众对直播的理解,比我们发表的关于直播的论文都深。“大哥”之所以理解得深,是因为“大哥”是钱堆起来的血泪,他们都很懂这个行业。大众媒体会把主播塑造成骗子,一个骗子骗一群傻子,其实不是。
02 “最好的办法是作为参与者,去理解她们的生活”
全现在:你们当时是怎么开始线上田野的?
董晨宇: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直播。我以前看过游戏直播,没看过真人秀的秀场直播。我就先试着待在一些大主播的直播间,看她们和粉丝怎么对话,粉丝怎么刷礼物。“大哥”刷一个礼物,我就去查这礼物值多少钱。当时就值3000块钱的一个礼物,一个“大哥”一下就刷了3万块的,我觉得他疯了。后来我发现小主播也有这样的,虽然没刷这么多,但是也有一两千人民币往外刷的。
我本来的研究方向是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分手之后,和前任在线上的一些勾连;再比如说旅居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如何使用微信。我觉得直播里的人际关系特别有意思。它冲击了我很多价值观,冲击了我对这个行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
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做访谈不太够。如果你是一位主播,直播的收入是你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我想在访谈中问你,你怎么看待给你刷钱的人呢?你会怎么说?你肯定会说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所以做这个研究可能最好的办法是作为参与者,去理解她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偏人类学的方法,我们写了很多田野笔记,但我们看到的东西大多没法写到论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主播线下的生活,聊到了他们的职业发展、人生困惑。这些东西不是访谈可以知道的。比如说某一位主播家欠了多少钱,他会告诉你吗?只有在你和她有长时间的接触,看到她直播间中来来去去的人之后,某一个触动她的时间点,她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全现在:最后深度接触的这些主播是怎么确定的?
董晨宇:是一个emerging(逐渐浮现)的过程。其实到现在我们也不觉得他们具有代表性。
客观的限制让我没办法接触到头部主播。大主播不会跟我聊天,没有时间。而且我去一个3万人直播间,我刷1000块钱,什么都不是,都排不到榜上。所以我们跟一些小主播接触,看她直播,帮她做场控,送她一些力所能及的小礼物。她是可以看到我的,因为直播间里就十几个人。另外一个办法是通过官方。但不论哪个平台的官方,都不愿意让你接触秀场主播们。
最后我们选取了5个主播,跟了2个月到9个月不等。其中有某直播平台头部公会旗下的三位主播,她们经常连麦PK,她们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人际交往圈。我们对这三位主播和她们的主要观众都进行了访谈,还有至少两个月的交往。
她们是直播行业中“散养型”的主播。也就是说你加入到我的公会,你赚10块钱,我给你5块,平台可能拿4块,公会拿1块,你如果老不播我会催你,但是我没有强制力让你去播。对于直播公司来讲,这些人非常边缘。你不播就不播,但你播了10块钱,我就拿1块钱,我躺着挣。
我们跟的三位中,有一位是从被重点培养的核心直播掉到了散养型主播,这种倒退,直播行业内部叫“播拉了”。另一位,是我们跟的时间最长的,从小主播变成了中型主播,但最近我听她说好像播得特别“拉”。还有一位,我们接触了两个月,她就退网了,不播了。
这三个主播和她们的观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观众交往圈。比如说作为A的观众,可能在A部开播的时候去看B或者C,说A开播了,你们俩赶紧PK,赶紧连麦。三个主播的和核心观众,他们彼此都认识。我最初的身份是A的场控,但是B的一位场控前几天还给我寄来零食,我们成为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五位中的另外两位是近乎全职的底薪主播。她们每个月的底薪是3000到6000块钱,要求一个月播28天,每天6个小时。她们拿的提成较少,10块钱会拿到2块5或者3块。但是底薪是播不够也给的。
全现在:场控具体是做什么的?
董晨宇:我们先说它的官方的功能,再说它实际的意义。
首先,官方的功能是作为管理员,你的ID前面有一个“管”字,是有一种身份感的。第二,如果别人说的话你不喜欢,你可以把他踢出去或者禁言,这是你的权力所在。第三,你的义务是给主播打赏。你不打赏的话,别人会说你管理员都不打赏,我们游客打赏个什么劲儿?但这也是有多有少的,有些场控本身就是打赏多的“大哥”。比如他今天打赏了三千块钱,主播马上给他加一个“管”字。
也有像我这样长期做场控的。比如我看一场直播,打赏几十块钱。每次PK的时候,我给她上一个几块钱的礼物,帮忙招呼一下,说大家来众筹之类的。主播如果指着我这几十块钱,肯定会死掉的。我要做的就是“破蛋”,激起大家消费的欲望。场控是主播的粉丝,同时也是主播的同事,但是没有薪水,还要自己贴钱。
如果我不想当场控,是不能自己把“管”字去掉的。这意味着管理员有权力,同时也有义务帮主播。要么付出时间作为一种劳动,要么付出金钱作为奖赏。我见过观众说你把我管理员撤了,我没法做。主播说不撤,你是特别重要的一位观众。这其实是情感上的一种约束。
全现在:当时你是怎么进入这样一种角色的?
董晨宇:从伦理上讲,我们一定要告知我们的被访者或被观察的对象,我们在观察或访问他。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说。比如你在做主播的时候,我进入直播间,说你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我叫董晨宇,我想做一个访谈。我试过,主播会觉得莫名其妙。我曾经给主播发一个私信,我说我是人大新闻学院的老师,她说我还是人大校长呢。所以不能这样干,这个职业特别敏感。
我们就直接进入直播间,去聊天、送礼物,这时候主播会表示感谢,她先提起来,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大学老师。她说大学老师也看直播?我们聊起来之后,我说不瞒你说,我们在做一个论文。这是我最开始的话术。但后来发现论文不能说,因为她们不理解。我只能说我们在做一个调研。主播就说这有什么可调研的?我们工作太简单了。这时候我说,我觉得你这里特别有意思,有研究的价值,同时我个人也蛮喜欢你直播的风格,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继续观察。我们如果在调研中涉及到你这部分,会把你的所有的信息都给抹去,没人会知道是你。如果你愿意做访谈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酬劳。如果我做你的场控的话,我也会给你刷一些礼物,这样一来,所有的这五位主播都知道我的真实的身份,这五位主播我们都进行过至少两个小时的电话采访。
全现在:所以这些主播播的内容是什么,观众是些什么人?
董晨宇:尬聊和才艺。有一位弹钢琴,另外四个是尬聊,其实大多并没什么才艺。甚至弹钢琴那个女孩最后也经常尬聊了,因为她发现一弹钢琴大家都走,大家还是喜欢聊天。
观众什么人都有,金融行业的,政府部门或者机关单位的,在校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如果我算其中一位的话,还有老师。这里面可能打赏最多的是小企业老板。
另外,我们拿到一个行业数据,77%的主播是女性,这个行业是女性主导的,甚至很多平台就是美女直播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做女主播。
全现在:底部、腰部、头部主播是怎么去划分的?
董晨宇:一般是按粉丝量和音浪来划分。比如说能不能每场在一万音浪以上。可能每场能稳定在两三万音浪,就是两三千人民币的礼物,拿到手大概是1000块钱,可能勉强算是一个腰部主播了。
但是这些是很少的,大部分主播都是小主播,可能播三个小时挣个四五十块钱。这个行业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挣钱。
03 “直播能够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研究者也没办法免俗”
全现在:你是一个研究者,同时又是场控,你觉得你的在场对于直播间里人们的表现有没有影响?
董晨宇:我们有时候太高估自己的价值了,他们根本不在乎的。甚至有的观众会把一些视频发给我,说这值得研究,你要是能研究的话,你拿走看看去。他们很好奇我在做什么。
我跟我访谈的这些对象接触时间长了之后熟悉了起来,我知道了她们很多的事情。质化研究者很难避免的是共情。你去平视她,发现自己并不是比她更好的人。每个人变成现在的样子,悲、喜、成功、失败,都有很多原因。
我想给她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这个群体的问题在于,大部分主播除了直播之外,看不到任何社会阶层上升的机会。有一个运营跟我说你一定要做直播,如果不做直播,你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么有钱的人。第二个问题在于,做了直播的主播,粉丝多的话,她们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中,会觉得怎么赚这么少,我明明坐在手机面前跟你们聊会天,一天就有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的收入。
但我没法去跟人家说这些话题的。我读了博士,拿到了985高校的教职,在她们看来生活滋润,衣食无忧,职业受到尊重,说这些,不是“何不食肉糜”吗?我对自己位置的反思在于,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她们跟我聊对职业的迷惘,后来我不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
全现在:做完田野之后,你在豆瓣上说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怎么讲?
董晨宇:作为研究者,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也尊重这个职业。幻灭感在于,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核心就是亲密关系的商品化。这是对人的异化。我们最早出卖体力劳动,后来出卖我们的情感。比如说空姐,她对你笑的时候是喜欢你吗?肯定不是,她是一种职业性的微笑。她在出卖自己的emotion(情感),而主播在出卖自己的relation(关系)。它是个关系劳动,出卖我和你的亲密关系来挣钱。所以我个人对这个行业可能是有偏见,我不喜欢这个行业。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主播,有那么一两个我没忍住,跟她们透露了,我觉得这没什么可隐瞒的。这个行业中有一些欺骗,甚至有些人把自己的真诚作为商品来去出售。
我可能把这个世界太理想化了。这个行业消失之后就没有类似的吗?也会有的。在应然的事情没法达到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实然。
作为一个批判的研究者,我们可以去批判它。但是作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这是主播们的生存之道。这其实蛮矛盾的。我现在也没法回答自己,我应该如何在讨厌这个行业的同时,又去喜欢这些个体。我会看到她们的很多抵抗,至少我访谈的这五位主播都很真诚,或者说她们是有底线的。
如果你直播,我陪你三个月,给你很多礼物,你对我不会产生一点感情吗?我想是个人就会有的。这种感情除了经济上的之外,难道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挺好的吗?你可能产生的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但有可能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所以主播们会跟我说一句话,她们说其实主播也是人,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也知道谁是对我们是真诚的,我们也想回报这种真诚。
这种信任不是为了写论文才有的,而是直播这个平台能够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是研究者也没办法免俗的。区别只是我作为研究者,我会更清楚这个平台的逻辑在哪里,仅此而已。
全现在:你提到很多次“真诚”。怎么去判断她们跟你的交流是真诚的?
董晨宇:交叉验证。首先是基于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第二就是我不会只访谈一个主播,她们即使都骗我,也不能都编一样的话。你不能要求被访者都跟你说实话,但是她们跟你说的有多少实话,往往是基于你们之间有多深的交情。
运营也是。有一个运营过生日,我在微信里面发生日快乐,她特别感动,说除了她最好的两个朋友之外,我是唯一一个祝她生日快乐的人。我觉得做田野首先要表达出你的真诚,否则你不能要求别人真诚。
对于受访者,我们第一能做的是保护他们的隐私,第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出我们能做的帮助。所以我说研究者可能需要做三点,第一是在表达之前去倾听,第二是在判断之前去理解,第三是在发表之前去关怀。发表是你的目的之一,不应该成为你所有的目的。
如果仅仅是发表一篇论文,其实并不难,但关键是你能不能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关怀?有一个主播,合同被欺骗了,我帮她找律师,我其实很难真的帮到她,但我会尽力去做这个事儿。我还想如果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能不能把它变成关于这个行业的解读,给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看,至少告诉他们,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陷阱,看他们能否接受。这其实是对劳动者的一种赋权。这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潜在的从业者能给予的一些帮助。
我前几天跟孙萍老师(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聊天,她做的是外卖小哥的研究。《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那篇文章引用了她的研究结果。我们研究者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把它写下来,也许能够有一些微小的个体有帮助。也许在某个时刻,你可以改变更大的东西。这可能是研究者所能努力的方向。
我们看到很多无奈的事情,我访谈过的一个主播自己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但我能改变什么呢?这个事是她自己的事,我帮不到的。作为研究者,你要首先承认自己的无能,在共情之后,承认自己做不到很多事情。这可能是我自己精英主义的坏毛病,所以我也在反思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全现在:她们在直播之外的生活,你怎么去接触?
董晨宇:直播间外,她们也有很多工作,她们要拍短视频,线下有公会去培训,她们要跟观众微信聊天。很多主播都会用微信小号来加观众,原因在于她们不想工作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有一个主播拿小号加我三个月之后,跟我说宇哥,你加我大号吧。那一刻作为研究者无比之喜悦。你仿佛获得了她的信任,进入了她的生活。
但加微信和不加微信,两种选择之间也有张力。其中一个我们做田野的主播非常不好接触,拒绝了好几次访谈。她说她不加任何观众的微信,也不给任何联系方式。我说我是你的观众,但是我完全公布了私人信息给你。我的目的其实是想做调研,这样也不可以吗?她说不可以。到了最后,我们的研究快结束,我告诉她,最后一个拼图就是你,你对我们至关重要,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是我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次访谈。她给了我一个打游戏用的QQ号,但是不能加QQ,就给她qq邮箱里发个信。我没想到,她给我回了非常长的邮件。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不加微信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举动。因为她告诉你了,你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观众,我不想跟你发展任何私人关系,这是多么诚实的一个人。她在回信中写了好长,跟我说她以前的经历,她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这次访谈反而是我们收获最大的一次。
全现在:你在豆瓣广播里提到,要把论文献给一位化名为Susan的主播。
董晨宇:她是我们跟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主播,跟我分享个人生活最多,可能也是我共情最多的一位。比如说她有一些职业上规划经常会问我,她可能做得不是特别好,但一直很努力去做。像是打不死的小强,社会阶层没那么高,没有背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一直在很努力地生长。可能这项研究之后,我就不是研究者了,而是她的一个朋友。
我觉得质化研究者很大的幸运就在于,有很多的机会,重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会更理解那些我本来一辈子都可能不会产生交集的人。
全现在:你们访谈都是线上进行的,没有见到真人,会对研究有影响吗?
董晨宇:从方法上来讲,的确是这样。人类学界有些人会质疑这种线上的田野,因为它不够有土壤性,不够接地气。我部分同意,因为研究者自身的“在场感”非常重要。我们想去见到这些人,非常有可能见到后发现照片跟真人不一样。但是我想为自己的argue(争辩)的一点在于,直播这个话题,其实不在场比在场的效果更好。只有当你们很熟悉,并且对方知道你了解这个行业,你很懂她的时候,这种身体在场的交流才是自然的,否则她们也不会主动跟你说。
当然,因为这些主播大多不在北京,等疫情结束之后,线下这部分我们一定会补上。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