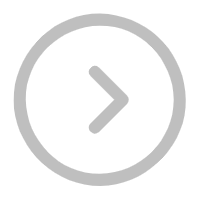导语植物肉确实可以在「健康」「可持续」的议题里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会是未来最好的蛋白质解决方案吗?
在四川长大,我常常会焦虑应该吃什么。倒不是物资匮乏,相反,天府之国可以选择的实在太多。作为一个有三十多年实践经验的杂食主义者,我推测自己的饮食偏好和三星堆的古人没多少区别:有什么就吃什么、众食材皆平等、没有主观的荤素之分。除了在体重超标的时候总是高喊需要寡油吃素,但身体还是在“平衡与和谐”的传统饮食哲学指导思想下,对肉一如既往地诚实。
也正因此,一些记忆深刻的吃喝之趣,都出现在为数不多的素食体验中。用熟面筋或冬瓜片炒回锅肉,是四川寺庙的经典仿荤手段;豆油皮仿鸡、鸭肉,茄子仿鱼,更是放之四海而皆有的斋菜做法。我对其中两种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魔芋染色,仿制素三文鱼刺身(来自一家经营“素怀石”概念的餐厅);另一个则更自然,产自宜宾的竹荪菌盖,展开之后,像极了一张金钱肚 —— 几乎以假乱真,入口咀嚼之后,才能识别不同。
现在想来,仿荤菜和分子料理的乐趣其实异曲同工 —— 所见非所吃。厨师用视觉和触觉的反差,挑战你的大脑,带来充满“意外”的食物记忆。不过,这种乐趣放在植物肉上,似乎就不灵验了。
一、植物肉,高级豆类加工制品
植物肉,简单来说,就是更现代的“仿荤”。将豆类植物中分离出的多种成分(比如蛋白质、脂肪等),用技术手段进行重组,组装后的产品颜色、口感和味道,从分子级别向真肉靠拢。为了使风味更像真肉,植物肉中还有各种不同种类的添加物,包括盐、油脂、香辛料、可食用的胶质以及增鲜剂。脱去所有营销语汇的包装后,它本质上是个高级豆类加工制品。
我原本以为品尝不同品牌的植物肉,会有类似于品尝不同产地、不同等级牛肉的乐趣。但在连续试完 4 家餐厅、5 个品牌的植物肉做成的菜肴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主厨们大多提供了汉堡肉饼、肉丸,以及肉臊子这几种形态,基本都是肉糜制品,风味上也都进行了更厚重的二次调味。这让我感觉眼下植物肉的功能更多是在模仿口感。
至于口感,确实很难吃出与真肉之间的差异,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植物肉在物理层面已经拆解到足够细碎的程度,属于“假碎肉(饼)”和“真碎肉(饼)”的比较,勉强达到了所见即所吃(与仿荤菜对标原材料的口感不同,吃植物肉时对标的是“真肉”,这让我下意识地变得苛刻)。而其它产品,除了一款植物鸡肉块有着第一口的迷惑性之外(随着咀嚼,感觉会越来越不像肉),几乎谈不上假肉和真肉的比较。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几个不同品牌的植物肉宣传资料,都不约而同地把推广重点放在“环保”“健康”“动物福利”这些概念上。加之目前植物肉的产品线和烹饪方法还存在局限性,这必然导致它会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我不禁联想到 2019 年的两部电影:《狮子王》和《阿丽塔》。当时引发的关于电影技术与真假边界的热议与争论,竟然又出现在了植物肉上:无限逼近真实的技术,是否真的能给受众带来感官的愉悦?
更深层的议题是,我们吃植物肉是否只是为了它吃起来像肉?
二、伦理素食主义的身份认同
与“环保”“健康”“动物福利”概念的绑定,让我们在回溯植物肉的源起时,很难完全抛开“素食主义”。但如果从印度阿育王、耆那教或者毕达哥拉斯说起,故事未免太长。就植物肉而言,我们可以把历史的进度条拉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15~16 世纪,是古典素食主义和现代素食主义的分界点。在此之前,素食主义更多地存在于宗教思想之中,这个阶段的素食者,大多是通过饮食行为寻求身份认同。随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逐步增多,基于“人类中心论”的基督教,开始与印度的素食主义进行互相观察。在识别了各自文化的优缺点后,逐渐融合与演化,衍生出不同的思想流派,并对世界运行规律有了各自的新理解。
发现万有引力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也在其中。他的另一重身份,其实是神学家。他在用物理公式描述世界运转规律的同时,也在试图从哲学和文化中提炼出这个世界思想和道德的普遍律法,从而创造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宗教。牛顿在晚年痴迷于研究炼金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为了启动欧洲化学、医学高速发展的一把钥匙。反过来,科学的发展,又为素食主义的演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16 世纪,医学素食主义从伦理素食主义中分化出来。很多人通过观察牙齿和消化系统,依据从解剖学中获得的论据,来辩论人的天性到底是草食还是杂食,并以此支持或反对素食主义。但这些思辨,主要还是基于宗教信仰驱动。真正让素食主义和现代医学接轨的是另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大航海故事:橙子与坏血病。吃素与营养健康的联系,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起来,并逐步发展出完整的医学素食理论体系。

Jalscha carla römer 联合 Lukas Ackermann 和 Andreas Spörri,在 2012 年发起了一个关于素肉的摄影项目。其中呈现的有着奇异外观的香肠、鱼饼等肉类其实都是由植物蛋白制成的,与如今的植物肉有异曲同工之妙。© Jalscha carla römer
从动物福利到环境保护,伦理素食主义的发展线路其实也很清晰。
从圣经中上帝嘱托亚当、夏娃关照身边的动物,到亚里士多德提出“动物为人类而生”,宗教和哲学的双重加持,让“动物福利”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根植于西方的素食主义思想中,只是后来它经过了多次演化。从早期的“宰杀动物会引起血腥暴力”,到自然主义的“人与动物存在灵魂的转世轮回”,再到“幸福死亡的动物能不能吃”,更多的是对人类“同情与仁慈心”特质的哲学辩论,是一条和科学(医学)发展完全不同的通路。

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中,狗狗 Hachi 在主人去世后每天一如往常般等他回家,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终其一生。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陪伴,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格外动人。© 《忠犬八公的故事》
在社会工业化浪潮的背景下,法国思想家卢梭观察到消费者与被消费者的距离逐渐疏远,提出“农业是不平等根源”理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受此启发,而后在《国富论》中提出关于人口的观点。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的肉、奶制品工业的不可持续论,集理论之大成,发表了影响至今的《人口原理》。虽然他本人不赞成禁止吃肉,但他提出的土地承载力(农作物的产量增长无法跟上人口数量增长)问题,恰恰成了伦理素食主义的绝佳理论基础:让自然更好运作、动物更幸福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养殖改为种植,以及,吃素。
植物肉,就是这场漫长的素食主义运动的最新出圈成果。不论是那些关注个体,在意动物福利的人,还是关心自然环境和生态健康的环保主义者,或者是单纯出于身体健康因素而吃素的人,都可以在植物肉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三、中国素食的宗教意义
2020 年,中国的“植物肉元年”。植物肉从科技新闻中走进现实,变成一个个品牌,迅速渗透进中国的餐饮消费市场。它正试图在这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度里,掀起第一波浪潮:从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国际连锁品牌,到湾仔码头、拉面说之类的快消单品,从各大酒店餐厅、商场餐厅,甚至再到主厨餐厅,植物肉产品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了中国市场消费者的视野。
这个在西方文化土壤中长出的“橘”,在东方风土里,是否变成“枳”?
大多数人对传统中国素食的第一印象,都与佛教有关。实际上,中国的素食记录远早于佛教传入的时间。作为以农耕起源的文明,果蔬在中国人食谱上的占比一直不低。《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其实就反映了中国人对肉食的态度:最初只是用作补益,谷物和果蔬才是主力和辅助。
而中国素食最早的仪式感,是《礼记》和《仪礼》中提到的,为父母服丧时,有长达三年时间,饮食上不能出现酒肉。父母下葬之后,只能吃谷物和水,随着各种祭祀仪式的进行,再逐步放开蔬食、瓜果和醋酱的限制。素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儒家用来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道家为了养生吃素,有一种关注营养健康的表象,但实际上它更加超然、出世,隐含着对成仙、长生不死的追求。道家最崇高的饮食理想,是什么都不吃。《淮南子》中提到:“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言下之意,服食空气,可以长寿;什么都不吃,就可以成仙。但这实在过于理想主义,道家选择素食,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折中 —— 谈成仙,总归还得和活人谈。
佛教的素食文化在中国出现得最晚,但持续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广。从汉明帝派出使节远赴印度,邀请传法僧到中国传播佛教教义开始,佛教素食文化经历了近 500 年自上而下的融合演变。直到南朝梁武帝写出《断酒肉文》,才借由佛教和政治的绑定,在僧人群体中得到全面推广。也正因此,在之后的 1000 多年里,中国的素食烹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风味流派。
有趣的是,在《断酒肉文》之前,中国的佛教并非纯素,而是对可以食用的肉类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比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吃的“十不净肉”,以及可以吃的“三净肉”“五种净肉”“九种净肉”(注:简单的说,“净肉”指来源和加工方式都符合佛教不杀生戒律的肉)。寺院菜系中的仿荤素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净肉”在行政法令下的变向延续。
从个体健康、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到儒家服丧、道家修仙和佛教的不杀生,东、西方的素食文化,仅仅只在“对动物的仁慈和同情上”有那么一点交集。从文化角度来看,对标传统仿荤的植物肉,无疑是个舶来品。它能否与咖啡一样演化成一种广泛的生活方式呢?时间还不一定能给出答案。
四、植物肉的悖论
与建筑学原理类似,食品公司把水、大豆组织蛋白、纤维素、油脂当做建筑材料,选择在最合适的位置使用最合适的成份,模仿搭建出与真肉结构非常接近的植物肉“建筑”。比如将蛋白质链接成长丝,用来模拟肌肉纤维的特征;用控制相分离、剪切和加热的方法,把植物的小球型蛋白,转化成类似肉中的长纤维结构;还可能对植物脂肪与植物蛋白质进行乳化,形成类似脂肪组织的构造。再加上能提供稳定高产的豆类单一化种植技术,以及食品工业化进程中硕果累累的各种调味、调色的添加物(当然是可食用的),让植物肉成为贯彻科技与工业化精神最彻底的产品之一。
现代科技让植物肉行业的信息壁垒远高于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很难仅仅凭借生产工艺信息就说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在生产端,有工艺上的等级区别(越要做得像肉,技术上就越难),在销售端,营销包装讲故事的空间极大。甚至连监管端,都还没有出台明确的国家标准(到 2021 年 8 月,仅有一份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牵头编制、由几个研究机构和各大利益相关食品公司参与起草的团体标准)。换言之,植物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具备相当有操作性的利润空间。
但是,从成都市场上不同种类餐厅中采集的数据来看,目前对植物肉有主动需求的消费者比例还是较小。
现阶段,成本还是植物肉扩张的第一道坎。相同重量的植物肉做成的汉堡肉饼,价格基本上与真肉肉饼持平(和真肉的等级有关,略微上下浮动)。在中国,传统消费者对植物性(加工)食材的价格锚点早已设定完成,很多人对植物肉的第一印象是“贵”,因而转身便选择了更传统又便宜的豆制品和蔬菜作为替代。
但根源还是来自于文化上的断联。服丧吃素的习俗,逐渐消失;念佛吃素不是主流。中国大多数传统消费者购买植物性产品,当然以追求风味为主。而这恰恰是目前植物肉的一大弱点:产品暂时还不能在更多场景中替代肉类。而食品公司也深知植物肉的优势与劣势,相对准确地把“环保”“健康”“动物福利”的概念,先投放至一小部分客群(一线城市,18~35 岁,接触过西方饮食概念),以期待由他们开始产生影响,并引领未来的消费风潮。
问题在于,从古到今,风味才是食材的核心特征。刚拆包的植物肉肉糜,口感有些黏腻,有咸味,咀嚼一会儿,会出现微弱的豆干味。一些肉块产品,还能吃出用来模仿动物肉味的香精味。坦诚地说,它的风味与真肉确实还有差距。那厨房有没有办法从风味这个角度,增强消费者的体验呢?我决定和几位主厨聊聊。
一位主厨直接表达了否定态度。他实在想不到有什么菜一定要用到植物肉,而且能比其他菜单上的菜更好吃。在成都经营餐厅多年,他遇到过不少对健康有要求的客人,他的现有菜单上有相当完整肉类和蔬菜门类,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确实没有必要在这个方向上再去创造新的需求。
一位主厨所在的是国际品牌酒店餐厅,按公司要求,在菜单里放上了植物肉做的菜,满足客人特定需求,但他个人对其中高达 20 多种的配料和添加物依旧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这些东西单独吃看起来都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但是放在一起吃,很难说会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是不太放心。因此他选择了一种折中方案:只采用一种肉糜,做成肉臊子形态,作为替代品使用。
一位主厨已经在植物肉上探索得比较远。菜单上的植物肉菜肴,从中西方各种肉菜中借鉴灵感,产品丰富,风味也都不错(如果不拿真肉做比较的话)。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偏好,他本身就有吃素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商业考量:植物肉这条赛道,竞争者还不多,经营起来压力不大,植物肉能让他接触到更精准的客群,从而为下一步运营一个更纯粹的自然素食餐厅做准备。
不过,植物肉要想在风味上通过主厨这关,可能还需要解决两个悖论。
第一是目前技术带来的烹饪方式受限、健康与风味的悖论。早期的植物肉产品仅能更适应煎、炒、炸等高温烹饪方式,留给厨师发挥的空间相当有限,但这个问题现阶段已经在逐步解决,适应中式烹饪中蒸、煮、卤、炖的植物肉也已经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可以期待的是,从《2021 中国植物肉行业洞察白皮书》来看,能适应更多烹饪场景、风味更强的植物肉,年内很可能就会出现。通过“蛋白质定向排列重组,做出整块植物肉”的 4.0 版本植物肉研发,也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看起来,在下一个阶段,植物肉将不再需要用浓厚或者强烈风味的酱汁(这部分的能量往往不低)和香料,去弥补本身风味的不足。主厨们能更好地在烹饪手段、营养健康和菜肴风味中,找到取悦多数客群的最优解。
第二是植物肉的「不自然」悖论。在普通消费者眼里,它是可以取代肉的食材,而在厨师眼里,它就是个工业加工制品。这很可能会导致双方在对菜品的理解方面发生错位。在一定程度上,真肉还是有一定的自然属性,比如有产地、等级的区别,也适用发酵技术,存在风土的影响。而植物肉始终还是距离自然太远。消费者需要重新修正对植物肉的风味预期。相应地,厨师也需要在菜品的自我表达和商业盈利中,选择和舍弃一些东西。
在阅读了各个食品公司关于植物肉的行业分析、推广文案及产品说明书之后,我观察到另一个问题是厨师的缺位。尽管有食品公司认识到了当下面向商家做销售,会比面向消费者更好,但营销概念依旧在围绕消费终端包装。除开金钱利益之外,厨师能从烹饪和销售植物肉中获得什么有益个人的、可沉淀的价值,始终还是不清晰。而现实是,工业化生产正在取代部分厨师的职责,比如工厂完成碎解,食品公司完成菜肴设计。借用名厨托马斯·凯勒的想法,在植物肉这条“生产 - 烹饪 - 消费”的链条上,只要一个会加热的人就够了。原本用烹饪来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厨师,在这场工业化运动的身份,无限接近于一个工具人。
五、风味、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传统生产被工业化取代确实是不可逆的趋势。而多个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植物肉也确实可以在“健康”“可持续”的议题里发挥重要作用。但植物肉会是未来最好的蛋白质解决方案吗?
2017 年法国纪录片《Food 3.0》具象化了一些新的蛋白质来源,重点关注了几个领域。一个是动物基的培养肉,这同样是一种实验室中产出的肉,利用奶牛细胞自己形成纤维组织,再长成肉。严格意义上,是无需繁殖和屠宰就能取得的“真肉”,真正的动物蛋白。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昆虫蛋白,昆虫的蛋白质比相同重量的肉要多 30%,只要打破人们一直以来将昆虫视为二等蛋白质的印象,它也将是优秀的蛋白质源。欧美许多国家、甚至连非洲某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尝试昆虫的养殖。
大卫·麦克伦茨在《未来食品》中,更详细介绍了第三种方案 ——微生物肉。这种肉的生产原理和植物肉又有不同,它是将碳水化合物废物作为能源,提取生长在大型发酵罐中的真菌支原体蛋白,与鸡蛋蛋白或者马铃薯蛋白混合,做成的肉类替代品。在欧洲,已经登上很多超市货架的阔恩牌(Quorn)素肉,就属于微生物肉。此外,一家芬兰公司已经研究出了利用微生物、空气、阳光和少量矿物质生产食用蛋白质的方法,这很可能会在人类移民火星的进程里发挥重大作用。
这些听起来像是来自科幻小说的食物,有些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的路上,有些则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也有很多消费者仍然在观望,他们或许同时也在关心另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拥有另一种未来?
蓝丘餐厅主厨丹·巴柏在《第三餐盘》中描绘了另一种未来的景象 —— 社群建立在人与人的互动之上。而可持续的社群,需要把定义延伸至土壤、水、空气、植物和动物。换言之,我们可以用更高、更完整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生态,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中的位置。在一个完整的土地伦理体系里,我们就有机会重构饮食 —— 重新种植适合于当地土壤的品种;恢复更好的风味,采用合适的轮作技术;避免食物减产的风险,用于修复土壤的轮作植物,也可以成为食物。无法进入销售链条的误捕的小鱼,以及海中的藻类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工业化而被放弃的某些次级部位(比如内脏),同样可以端上餐桌。风味、健康、可持续,不再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这看起来几乎就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一直秉承的理念,意外的是,它竟然在一个西餐厨师的烹饪哲学中表现出殊途同归。事实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未来食物与农业-趋势与挑战》(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 Trends and Challenges)中,提出了 21 世纪人类食物和农业发展的若干趋势和挑战,其中关注到了反刍动物的温室气体排放、食品健康等食物行业现状,而这些的确是植物肉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这份报告的总体视角还是基于完整的食物生态,其底层逻辑正是遵循着土地伦理。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其实远比“环保”和“营养健康”议题更复杂。比如: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可以为小规模生产者和无土地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帮协机制,又能为本地社群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扶持。单一化种植有没有可能调整方式,避免过度利用土地以造成不可持续的伤害;是否可以从依赖化学投入的单一化种植农业,进化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管理等等。这是一系列巨大的话题,目前远非一个植物肉产品所能承载。
对植物肉的消费者而言,这份报告相当有参考价值。它能带来更多思考和启发,进而完整我们对食物生态的认识。在面对各类植物肉营销信息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被单一信息源困住,可以尝试通过更多的视角去审视这件产品,以确定自己在植物肉上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在一个更完整的“健康”“环保”“可持续”生态上,发挥最大效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oodWine吃好喝好(ID:FoodWineChina),作者:张秦瓯,编辑:刘树蕙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